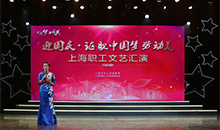一叶访谈丨李园:我和舞蹈治疗
——李园

李园
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2001年至2016年任教于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编导系;2015年攻读美国舞蹈治疗协会(ADTA)R-DMT注册舞动治疗师课程;2016年攻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三级,二级心理咨询师课程。
拥有30年专业舞蹈背景,15年舞蹈教学的工作经验,擅长教授舞蹈即兴及编舞技巧等课程,曾独立创作多部舞蹈作品,涵盖舞剧,音乐剧,多媒体交互,实景演出等多种艺术门类,并多次受邀赴欧洲,亚洲多国访学及艺术交流合作,其中指导多部舞蹈作品荣获国家级奖项。
2015年,因缘际会,我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从业的心理咨询师。记忆中,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私人诊所,一间15平米左右的房间,布局很温馨,有棵大型的绿色植物,带有图案的地毯,一张躺椅和一个沙盘桌,书架上除了一堆关于心理学领域的书籍之外,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实景模型。他在我们对面,坐在一张很有质感的皮椅上……这样的摆设,直到后来我学了心理学才明白,那是一间心理咨询室应该有的样子。不记得聊了多久,也不太记得都聊了些什么,但是我却深深记得他问我:“你对心理学感兴趣吗?”那个时候心理学这个概念仅停留在我在大学期间读过的一本弗洛伊德写的《梦的解析》,十七八岁的我为什么会读这本书已经模糊了,只记得——很难读。紧接着他又说:“我认为你有做心理咨询师的潜质……”我很疑惑了,他在我身上发现了什么?一直以来,我都是个对万事万物保持好奇心的人,那次见面结束后,我做了些功课,大致了解了心理学以及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然而,我更好奇的是,他为什么会认为我有做心理咨询师的潜质?(当时的我非常无知的认为,他应该是觉得我很!能!说!)大概过了半个月,我再次联系了他,我想我需要知道答案。
那时,我已经在上戏工作了近15年,主要从事舞蹈创作和教授舞蹈编导理论,虽然我很热爱教师这份工作,但是从入职那天起,我就认为总有一天我会离开,对于外面世界的好奇心驱使我不断的探索各种可能性,只是不知道何时,以何种方式来结束。他的话像一味引子,打开了我决定重新出发的大门。在他的引荐下,我认识了中国舞蹈治疗的“黄埔军校”——亿派学院的项目负责人。舞蹈治疗作为心理学中艺术治疗的分支之一,是以舞蹈的形式对个体进行心理干预的治疗手段,对于有舞蹈背景的我而言,似乎是进入心理学最合适的路径。亿派学院严格按照美国舞蹈治疗协会的课程设置,要求每一位有学习意愿的成员必须先体验一次舞蹈治疗的工作坊,以此确保是否明白舞蹈治疗的具体操作方式,以及再次考量自己的学习意愿。
我的第一次体验课程在成都,由美国BC-DMT高阶舞蹈治疗师Linda老师授课。前两天的课程里其中有一个环节——whitehouse,即真实动作。几轮练习下来,我都有种莫名的不满足感,欲言又止的困惑和深深的困顿,却并不清楚问题所在。下课前Linda要求我们去思考:身体被什么控制而失去了真实的表达能力?当下的舞动是身体真实的表现吗?我反复思索:作为一个有着专业背景的我,身体真的还保留着最真实的动作表现吗?所幸,我找到了令我困惑的原因——练习过程中,我并没有真的感受当下,没有尊重我的身体表达,亦没有真的做到真实动作。其一,同期参加体验课程的大部分人是心理咨询师,还有个别以自我疗愈为目的的社会人员,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真的舞蹈?为了在团体里显得不那么具有舞蹈性,我有意识的控制住了自己身体,以及自己最擅长的肢体表达能力,扮演一个貌似没有舞蹈背景的爱好者,只是为了看起来和其他人差不多。其二,作为舞蹈工作者,对待身体,一直像对待一件工具,是与其他人联结,沟通和表达的工具,它被我们大脑驱使着学习各种技术,探索肢体的可能性,以完成我们需要去完成的事情,身体已失去了身体本身!想明白这些原因之后,当我再做这个练习,闭上眼睛的那一刻,被我大脑控制,压抑了多天的身体,摆脱了束缚,表现最真实的当下,让动作从身体里流出来,不在意是否与其他人的不同,不去想结构和主题,也不去想发展和变化,所有原来停留在大脑里的,关于肢体运动的技法被我抛弃到了一边,只是身体,仅仅是身体,那种不用思维控制身体的感觉,非常棒!也是我第一次真切的意识到身体有它自己的感受,脱离大脑控制之外的,甚至是被大脑遗忘或抑制的感受——尊重身体真实的表达是我学习舞蹈治疗的第一个觉察。

而让我决定开始学习舞蹈治疗是真实动作练习中引发的对于力量的感受。有一轮,我作为观察者,坐在教室的角落,聚焦在我需要观察的动者身上,时间一点点流逝,当我用余光留意到另一位动者靠近我时,我的身体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愿。记忆里,她非常轻,且试探性的靠近我,仅用手指在我胳膊上游走 ,然后是腿部,最后是头部,或许她是想通过衣服材质等特征来识别出我是谁?我以为她在确认我的观察者之后会离开,没想到她坐了下来,余光可及之处,只是静静的坐着,但是她的脚紧紧的靠着我的脚,后来回想起来,可能当时身体的接触已经把我们连接在了一起。那个时候,我观察的动者已经流动到了我的左前方,虽然老师强调要全身心的聚焦在动者身上,而我的眼睛也至始至终都没离开过我的动者,但是,另一个动者的存在就像我视线之内的阴影,无法回避,我能做到就是不断提示自己,聚焦动者。然而她并没有完成她的身体表达,她一点点的靠近过来,整个后背依靠在我的大臂和腿部外侧,我能感受到的是力量,很强烈的重力。当下,我身体也回应了一个坚实,稳定的身体状态,我想要支撑住她,让她感受到被支持和可以信赖。接下来,她开始不间断的用重力靠向我的身体,有冲撞,有摩擦,有依赖,也有短暂的分离,而我已经无法离开,只能那样坐着,不得不去承受那些力量。不知道过了多久,或许她累了,停止了动作,蜷缩起来,躺在我的脚边,就在那一个瞬间,我的眼泪根本控制不住的留下来,而我自己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的眼泪一直在留,而我却冷静的一边看着我动者,一边停不下来的思考,我的眼泪为什么而流淌?没有答案,因为我所有的意识,除了身体,全部在跟随我的动者,我的思绪里根本没有我的故事,但是,眼泪从哪里而来?像一个不知道去哪里寻找答案的问题!练习结束,我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的进入分享环节,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下课前,Linda 老师对我会心的一笑,使我确信,她清楚的见证了我的转变,也见证了我没有分享出来的眼泪。
回到房间,我不停的踱步,清楚地知道自己内心的情绪被莫名的东西搅动了起来,而且是在我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是什么?我不停的回忆,重新梳理每个瞬间,如果不是故事,不是事件,也不是人,那个当下,我能感受到的就是力量——强烈的力量,沉重到让我失控的力量!
在此之前,关于鲁道夫·拉班的力效理论,是我再熟悉不过的。15年的编导教学过程中,我反复讲了无数遍,做了无数次的示范讲解,但是,我真的用身体真实的感受过力量吗?当下,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身体被大脑支配了太久,它储存了许多未被消化和释放的情绪,可我却从来没有给过它机会去表达和宣泄,当它脱离大脑的控制,单独存在的时候,另一个动者的重力深深地刺痛了它,滞留在身体里的情绪被激发出来,我的眼泪为我身体里存储的记忆而流淌——倾听身体真实的声音是我学习舞蹈治疗的第二个觉察。

第三个觉察——表达的方式,彻底改变了之前我对于治疗师这个职业浅显的认识。与那位从业的心理咨询师交流过程中,一直以为自己清晰的观点表达是他之所以认为我有从事咨询师这个职业潜质的根本原因,于是,带着自以为是的良好的沟通能力来到成都。课上,我们时常需要分组或集体讨论,分享个人的动作体验以及情绪感受,老师要求我们认真倾听,不去评判,不发表带有个人主观揣测的观点。同期体验课程的同学有小部分社会人员,他们带着自己的议题,以自我疗愈为目的参加舞蹈治疗工作坊,分享过程中,并带有引发情绪的具体事件的详细描述,在他们表述问题的当下,我的大脑也飞速运转,有时很想制止她停下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有时针对其中某些事件内心迫不及待的想给出一个建议。但是,这些内心的想法被老师之前设置的规则所限制,而这些限制在时时刻刻挑战着我的思维模式和表达习惯,使我的语速不得不慢下来,大脑在组织语言结构的同时,筛选出恰当的措词,不带有评判性的论断,更不要像做老师一样给出自己的建议,几天下来,我已经到了张嘴都能感觉到累的程度!从事编导教学工作15年,习惯性的带着自己主观的看法评判学生的创作作品,挑剔,甚至是苛刻,总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固执的认为这样是对学生负责,这样对他们更好,并没有给予他们太多的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又或者说,没有停下来,去等待。许多时候在他们还没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的时候,我已给出了答案——这样是可以的,那样是不可以,在抱怨是什么扼杀了他们创造力和表达能力的同时,我自己也变成了拦路虎。
体验课程结束过后,带着许多新的认识和困惑,我决定开始学习这个专业。二年多的历程,伴随着莫大的痛苦和欣喜,时常感觉自己掉进了情绪的黑洞,许多自认为被解决的议题不断出现,强迫你不得不去面对和思考。而后,心底出现一缕阳光,足以驱散内心的不安和惶恐,站到一个新的台阶上重新出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每次浮出水面的背后都是一次深深的下潜,直到身体的通道被冲刷干净。从业的咨询师朋友告诉我:如果你真的准备从事这个职业,就代表你已经决定要深潜到自己内心去探索,那些黑暗和光明都在的深渊!我犹豫了,害怕了。至今为止,我依然不确定我是否真的适合,或者说我真的已经做好了从事舞蹈治疗师这个职业的准备。但是,我会遵从自己的内心,重新认识身体,重新认识自己,继续一段即熟悉又陌生的旅程,只希望,离真实的自己更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