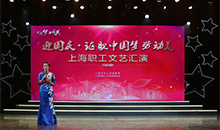一叶访谈丨畅游在巴洛克音乐海洋中的鲁特琴师

张洛菩 :
旅德鲁特琴、吉他演奏家、上海恰空古乐团成员、柏林Baroque Sequeza乐团的成员。
2009年秋远赴德国,先后在达姆施塔特音乐学院、柏林艺术大学随德国殿堂级吉他大师Tilman Hoppstock、Thomas Müller-Pering学习古典吉他,获得教育与演奏两个专业方向的硕士学位。后跟随鲁特琴演奏家Björn Colell在柏林艺术大学与纽伦堡音乐学院攻读早期弹拨乐,期间曾作为访问学者于荷兰海牙皇家音乐学院随鲁特琴演奏家Joachim Held和Mike Fentross学习。
他的演出形式多样,演奏曲目题材广泛,以独奏、室内乐等形式在德国各大城市以及法、意、荷、捷、瑞士、西、美、土耳其等地举办音乐会。张洛菩是第一位在欧洲学习并掌握近乎各种欧洲早期弹拨乐器的中国人,并参与多个欧洲古乐乐团以及巴洛克歌剧剧目,研习德法意巴洛克早期的室内乐作品以及早期器乐独奏作品。
我的父亲和姑姑是痴迷音乐的,他们可以把外国民歌三百首倒背如流,中国歌谣曲来张口,我得此禀赋,能很快学歌哼调,识谱比认字还快。学校的音乐老师是师专科班,对我格外青睐,把全校罕有的才艺孩童聚在一起组建合唱团、兴趣班,交流多了,即便井底的青蛙也能取长补短。父亲在省外贸工作,他见同事的孩子跟歌舞团的艺人学习双簧管,于是带我去咨询,那位老师见我年幼气短,于是建议建议我学习钢琴。那时的普通家庭是买不起钢琴的,是我大姑姑得知某幼儿园淘汰下来一架电钢琴,于是果断买下,因我家居住面积狭小,所以钢琴放在她家,每周末去练琴加学习。我的钢琴老师是她家附近的一位怪老头,其父母曾是资本家,家传的西式教育,琴棋书画都有建树,家里竟有九尺的英国老三角钢琴和民国买入的欧洲油画。他年轻时在文革浩劫中遭抄家批斗,心灵受过刺激,是以性格极为怪癖,使得他话说颠三倒四,教学少有章法。心情好时,他还教过我大提琴的持琴姿势,丹青画竹的运笔技巧,甚至是魏碑书法的基本功,赠我水墨宣纸;心情不好时,蒲扇般的大手掌就猛地打下来,然后把谱子猛地摔出,脸色怒气环生。我回家看电视上的东邪黄药师,因为发火而挑断了徒弟们的脚筋,我生了畏惧,加上平日难以练习,所以就此放弃钢琴,如今想来,是一大憾事。
学校的兴趣班做出了点儿成绩,校方得到了乐器厂的赞助,其他学校优先得到钢琴和军乐团的乐器,留给贫民小学的,只有吉他了。我始终记得那些残次品动不动开裂崩弦的场景,让我今日每次换琴弦,都会下意识地认为琴弦快断了。后来一位打扮时髦的男士来访,露了一手古典吉他,我见状上前求学,于是他成为了我 启蒙老师。六年级时我转学到了一个顶尖的私立学校,学校里都是各个公立学校转过去的小朋友,家里条件普遍殷实,我惊奇地发现,都是同龄人,他们身上几乎都有音体美劳的小才华,于是我不甘落后,努力练琴,谁知跟吉他结了这么深的缘分。


Hoppstock是巴赫专家,对早期音乐研究有着十分独到的研究,而我很久之前曾在国内的盗版音响店里买到很多外文原版的打孔碟,除了巴赫,泰勒曼,维瓦尔第之外,就是两张由瑞典人Jakob Lindberg录制的鲁特琴唱片。那时我已经迷上了这个乐器的音色,希望能亲自见闻抚摸这个乐器。在Hoppstock的影响下,我在吉他上演奏的古乐越来越多,后来干脆跟Olaf Van Gonnissen教授辅修了鲁特琴,梦想既成,从此一颗心投了进去,再无回旋余地。
我在达姆毕业之后考入柏林艺大,跟随Thomas Müller-Pering先生继续深造吉他,同时跟Björn Colell双专业鲁特琴,因为两个乐器的特性,是的演奏技巧和理念有时难以兼容,所以我拿到第二个学位之后,才决心暂且放下吉他,继续研究鲁特琴。我的恩师Björn Colell曾经是伦敦皇家音乐学院Jakob Lindberg教授的得意门生,而我十几年前听到那张打孔碟,便是Lindberg录制的。
鲁特琴是冷门专业里的边缘乐器,也是很难的乐器,只有在部分的欧洲音乐学院才有古乐专业和鲁特琴专业。传统的学业设置,学习者需要掌握文艺复兴鲁特琴、巴洛克鲁特琴、西塔隆尼琴、巴洛克吉他等四个不同类型的鲁特琴,他们彼此虽有关联,但是在演奏风格以及手法上有时却大相径庭,除此之外,如果有条件,可以学习中世纪鲁特琴,维埃拉琴以及罗曼吉他。除了独奏之外,鲁特琴演奏者要对通奏低音极为精熟,参与大量的室内乐演奏,曲目范围从文艺复兴早期到古典主义早期。如果是本科阶段,还有专门的古代音乐史,宗教音乐等极具方向性的课程;根据学校教师本身研究的重点,也有会装饰音、通奏低音、乐器法、风格学等专业。可以说是自成的一个特殊的专业小世界。

张洛菩 :
我在德国的前两个硕士都是有关吉他的,从就业对象来看,国内的吉他教育正蓬勃发展,我也愿意投身其中,献绵薄之力;鲁特琴以及欧洲古乐,是国内文化市场和音乐通识上的薄弱环节,我从3年前开始就在举办鲁特琴音乐会,我也是中国首个本真古乐团“上海恰空古乐团”的成员,成功举办了多场风格及形式不同的室内乐音乐会,我也在撰写学术文章及公众号,多从角度介绍早期弹拨乐器,尤其是补缺国内吉他从业者对鲁特琴等早期音乐的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