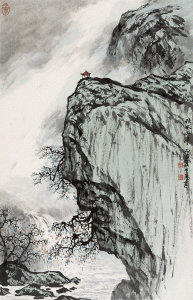一叶访谈丨周阳高:书画山水,对话心灵
画了近五十年的山水,越来越觉得其实我并不是在画山水,而是在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对于绘画,其实我只有寄托,没有追求的。我认为真正的艺术不可能是由刻意追求获得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即兴偶发的……
浙江黄岩人,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审,原《书与画》杂志主编。1965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国画系山水专业。1980~1990年先后五次在上海、镇江、西宁、厦门等地举办个人诗画展。1993年4月在新加坡举办个人书画展。1998年1~3月连续两次在德国举办个人书画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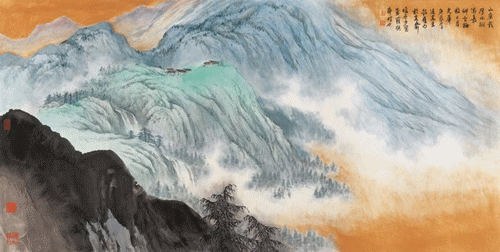
画了近五十年的山水,越来越觉得其实我并不是在画山水,而是在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曾在我的个展前言和一些文章里说过:对于绘画,其实我只有寄托,没有追求的。我认为真正的艺术不可能是由刻意追求获得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即兴偶发的。宁静而闲适地画出的作品,往往会达到较好的效果,有时甚至是只可有一而不可有二。有人会说这只是古已有之的“文人画”作风而已,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好。
在我以这样的心态作画时,会获得最放松最解脱的感受。天地和合,万物如一,周遭的声响和动静都似有似无,瞬息即逝。惟有笔下的树石云水奔涌会集,各就其位,凑泊成趣。其实,这正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心灵所向往的某种境界。而当这种境界果真呈现在你面前时,该是一种多么难得的满足与慰籍啊!可惜这种时刻实在是太少了。常有人说绘画之艰难不足与外人道也,其实要做好任何事都是不容易的。绘画之难、艺术之难,就难在不可以对待事功的态度对待之、追求之。它是各类因素此消彼长、偶获齐集,并厚积至溢、薄发如丝而成的。这里有一个“缘”的契机,“情”的激荡,“性”的躁动。画于不得不画时,止于不得不止处,这才是绘画,才是创造;是劳动,是娱乐,也是享受。于是心灵获得了满足,进而或许有某种启迪,孕育着下一次绘画的降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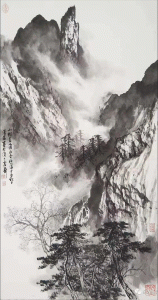

我从事书画收藏已三十余年,与不少著名书画家、书画大师打过交道,也藏有不少周先生各个时期的作品。像他那样不为市场趋求所动,不甚计较画价收益而一意执着于自己艺术追求的画家还真不多。他发展变化了的没骨青绿山水很受藏家欢迎,而他却不接受预订复制,不愿为金钱所役,在当今物质至上的浮华尘世,显得尤为难得。

十一年前,我为编印《应野平画集》而在上海书画出版社结识了他,那也正是他潜心于山水画研究,在技法理论和技法传授上都结出丰硕成果的时期,三四年间,他先后出版了《经典山水画法》、《名家临名画·唐寅》、《名家临名画·李唐》、《中国画技法通解·松柏画法》、《中国画技法通解·雁荡画法》等五本专著。尤其对李唐《江山小景》、《万壑松风》、清溪渔隐》三图的临摹、研究和撰文分析、讲解,使他对中国山水画发展到高峰期后的演变走向和脉络条理,以及李唐在这一历史性关节点上的特殊贡献、特殊意义有了更为深入透彻的理解,对确认和坚定自己的绘画道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藏界追逐浮名、地位、时价的混沌状况相似,画界也追逐这些光怪陆离、虚幻不实的时髦,却很少有画家知道自己究竟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在历史上是否可能有一席之地?周阳高先生对此却有着清晰而坚定的认识和定位。在他《画集》的自序中说:“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考量自己或许在历史上可能的位置,使自己清醒,使自己警策,使自己努力。”也许正因为这样,使他在名和利两方面都显得甚为超脱,甚为从容而淡定,不周旋于任何热闹场合,耐得住寂寞,不怕被人遗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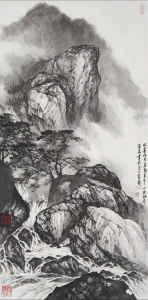
在他的精神王国里,除了绘画,更有诗词和书法两大爱好。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用在周阳高先生身上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他十七、八岁在美专求学时就能作规范严谨的格律诗词,临习字帖往往一写就是四五个小时,他说习字使人特别沉静安稳,阅读更是他的一大爱好,他说读到一本好书真是无上的享受。从他近期的诗句“读书快意如鞭马,经世何妨倒骑牛。”(和鲁迅《自嘲》四首之一)中可以一窥他的真切感受。有一次闲聊中,他说他看到一份俄国 屠格涅夫著作的中译本书单,居然全都读过时,他自己也吃了一惊;一般读书人视为畏途的歌德《浮士德》,他读过二遍……至于近数年间的《往事并不如烟》、《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苏联解体亲历纪》、《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七卷本)、《万历十五年》、《货币战争》等等,他全读过。更不用说唐诗宋词的阅读背诵量了。清代的纳兰性德、王仲则他都不忍释手。有一次在应邀出席上师大的一个座谈会上,他说“要了解自己的知识结构,有意识地作些必要的补充调整,不要赶时髦,不要在乎别人在干什么,要有自己的定力,才能选择正确的绘画道路。”他这样说时,看着听众茫然而游移的眼神,自己也觉得迂腐,但这又确是走向成功的不二之选。问他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时,他说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你总不能问这一部分生活有什么用吧?生活中不能有那么多直接的功利和目的,长期的大量的阅读会铸就一个人的人格,最终沉淀在艺术作品中,决定其价值高下的就是作者的人格。

与广泛阅读各类中外名著、回忆录、传记和与时政相关的书籍相比,他对画史画论的阅读就少得多了,甚至大多限于为写文章而作的某些检索。他认为传统的画论不是失之于宏阔虚泛就是失之于繁琐细碎,少有规律性的识见可寻。因为写画论的人自己不画画,或画得并不深入,缺乏真切的体会,而画画的人,画得好的甚至触及了画史的人又不写画论,致使“画”与“论”处于脱节游离状态,流行于世的说辞往往隔靴搔痒,浮泛无着,或艰深晦涩,似是而非。如郭熙《林泉高致集》这样有真知灼见的著作实在太少了。而通过他自己认真临摹、深入研究和近50年的创作实践,提出了如下明确的观点:①宋、元绘画是两个不同的范畴。②李唐创制的皴法有繁、简两体,繁体综合运用点线面的皴法,史称刮铁皴,简体只用面皴,才是斧劈皴。③山水画皴法完成点线面的发展后,转向勾皴染点四步骤先后顺序的变易上来。并以李唐《清溪渔隐》图中的画树法、唐寅《山路松声》图中的画石法等名画来证实之,进而再举出清初石涛《仿倪瓒山水》册页中的作品以颠倒先近后中再远的景物描写顺序,致使笔墨干湿互破,浑然一体,造成分外晕化滋润的效果,来说明:④山水画笔墨变化的创造发展已臻于极限,要勇于承认这一基本事实,不要盲目希冀新的发明创造等。(2009年8月9日《解放日报》文博版)这些迥然有别于时髦思潮的见解,从未见之于前人,也未见于之今人的论述,是他数十年如一日浸淫于传统巨流中(现实状况只能是潜流,但它毫无疑问是顽强地存在着的)探寻笔墨之道的真切体会,从中也明确了自己继承李唐未竟之业,参以当代人对自然的观感,着意于对山石山体山峰的描绘,使他的山水画在李唐之后八九百年的历史空缺中崭露头角。难怪谢稚柳先生在1996年就撰文盛赞周阳高的绘画道路是“理性的选择”,称“他的画在严密坚实的造型中透射着理性的智慧之光,这就是所谓的宋画精神,阳高得之。”(1996年9月《东方航空》)

尽管周阳高先生在山水画领域里开辟了自己特有的天地,但他不张扬,不喧哗,也不推向极端,在蕴藉稳健的大道上悠然慢步,云蒸霞蔚,清和祥瑞。他说山水画要的是大气象,不在乎小趣味;要有感人的诗意,而不要扰人视听,乱人情志;要贝多芬、莫扎特,不要摇滚。这又不能不说他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了,看他《高斋戊子吟草》里的书法,有开张飞动的精神,却几乎完全收缩在规范内敛的笔划和结体之中,他的诗也婉转平和,没有骇人的字句,惊人的声调,却隐藏着一颗坚定自信的内核和空阔无前的境界。